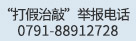
中華文化推崇對稱之美,體現在文學上,便是文辭的偶對。先秦兩漢文學中偶對已日漸增多,時至六朝,駢儷發展成為具有時代意義的修辭方式。劉勰《文心雕龍·麗辭》考察的正是這一文學現象,提出“四對”說:言對、事對、正對、反對。其中“事對”乃“并舉人驗者也”,即并列對舉前人事跡以驗證作者觀點。兩事“并舉”,雖取決于所表達的內容,但這種選擇并非作者對“事”的任意使用,而是對所引人事有一定判斷后,擇取最為恰當的事典。因此,“事對”在藝術價值之外,還蘊含以往不被注意的文學研究資料。當我們考察漢賦紀事經典化這一命題時,“事對”藝術,因其“事”與“對”的雙重特征,成為文士展現賦史認知的特殊途徑,構成漢賦紀事經典化的重要一環。
六朝“事對”與漢賦紀事的接受
六朝去漢未遠,奠定后世對漢賦紀事的基本認知。六朝“事對”也在確認賦家地位、凝塑故事內涵上,具有典范意義,極大影響后世文士的文學創作。
“事對”對賦家地位的確認,在《文心雕龍》中體現明顯。如《神思》篇論“思遲”:“相如含筆而腐毫,揚雄輟翰而驚夢,桓譚疾感于苦思,王充氣竭于思慮,張衡研京以十年,左思練都以一紀。”劉勰標舉六事,可分為兩兩相對的三組:相如與揚雄,桓譚與王充,張衡與左思,并舉之人具有相似的事跡與文學地位。其中,又以馬、揚最具代表性。徐陵《謝賚麕啟》:“臣昨既陪羽獵,仍宴上林,固謝長卿之文,彌慚子云之賦。”置身于宮廷場域中的徐陵,自覺與馬、揚作賦相比較。虞世基《講武賦》同樣由馬、揚引出自己作賦:“昔上林從幸,相如于是頌德;長楊校獵,子云退而為賦。”這種自我標榜,在楊素《贈薛播州詩十四首(其七)》中簡化為:“上林陪羽獵,甘泉侍清曙。”馬、揚作賦紀事的并舉,確立了賦家宮廷作賦的基本行為模式。
六朝“事對”對紀事內涵的構建可以“賈誼”為例,集中于“年少才高”與“失志被謫”兩點。“年少才高”體現在與終軍的并舉。孔融《薦禰衡疏》:“昔賈誼求試屬國,詭系單于;終軍欲以長纓,牽致勁越。”用兩典凸顯禰衡年少、才高、志大。這種用法為潘岳、江淹、江總等人祖述,至隋代碑文便以“賈誼登朝之歲,終童奉使之年”凸顯墓主陳茂年少入仕,成為贊頌套語。“失志被謫”則在與屈原并舉中最為明顯。孫萬壽《遠戍江南寄京邑親友》:“賈誼長沙國,屈平湘水濱。”屈、賈在《史記》中同傳,皆曾身處湖湘,二人并舉客觀上提升了賈誼的文學地位。
漢賦紀事在六朝“事對”中被濃縮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事典,促進了漢賦紀事的傳播與賦家地位的提升。初唐類書《初學記》小類之下設置“事對”名目,是此藝術手法廣泛應用的有力證據。唐代以后隨著近體詩、賦的成熟,“事對”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超六朝,征引漢賦紀事也更為復雜、多樣。
唐代“事對”中漢代賦家的獻賦與失志
面對六朝人確立的典范,唐人“事對”凸顯漢代賦家獻賦者、失志者兩種形象。唐代獻賦書寫仍然盛行。如潘炎《漳河赤鯉賦》:“事稱嘉瑞,匪琴高之所乘;詩有樂胥,似相如之獻賦。”景龍三年(709),唐中宗巡狩途經漳水時見赤鯉騰躍,潘炎作賦頌美,自比相如獻賦。令狐楚《漢皇竹宮望拜神光賦》:“備禮告天,帝既逾于孝武;觀光獻賦,愚竊慕夫相如。”則以漢比唐,敘寫當朝典禮。可見在宮廷語境中,漢代獻賦已成為唐人自覺的文化記憶。
一旦脫離宮廷,獻賦書寫又轉向其他面向。白居易《及第后憶舊山》:“偶獻《子虛》登上第,卻吟《招隱》憶中林。”此詩作于進士及第后,正是白居易人生極得意處,他卻轉而吟誦左思《招隱詩》。淮南小山《招隱士》本是招隱出山,左思《招隱詩》則寄寓退隱之志,王子猷大雪夜吟《招隱》又有名士之樂。白居易將之與相如獻賦并舉,透露出唐人在出處進退時的矛盾心理。
唐代科舉取士,大部分文士并不能像白居易一般順利取得功名,因此,漢代賦家的落魄事跡令他們感同身受。命運坎坷的賈誼、桓譚、馮衍、崔骃、梁竦、趙壹等人姑且不論,即便是被視為“獻賦”代表的馬、揚,“事對”中同樣不乏失志書寫。駱賓王《帝京篇》:“馬卿辭蜀多文藻,揚雄仕漢乏良媒。”通過揚雄無媒境遇,彰顯自己十年不調的無奈。楊炯《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》也將馬、揚視為不遇代表:“揚子云之才藻,空疲執戟;馬相如之文詞,猶勞武騎。”唐代的馬、揚相對,從賦學地位相等演變為精神內核相通。
唐人雖仍艷羨漢代獻賦故事,且在宮廷語境中自比馬、揚,字里行間充滿參與帝國政治的自豪感,但唐詩中吟詠更多的是獻賦無成的落寞,以及思考出處進退時的矛盾。漢賦紀事普遍被作為失志典故,與唐人產生心靈共振。
唐代“事對”中漢代賦家的名士化
唐代“事對”還將賈誼、枚乘、相如、揚雄、崔骃、馬融等賦家與魏晉名士并舉,塑造其符合唐人審美的精神特質,這與六朝對漢賦紀事的接受有一定關聯。正如唐人仰慕魏晉名士,六朝人也將漢代賦家作為效法對象,嵇康《圣賢高士傳贊》便將相如塑造為“越禮自放”的高士。唐人在“事對”中繼承六朝精神風尚,促成漢代賦家的名士轉向。以相如為例,“事對”中的名士化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。
其一,風神描摹。李白《對雪醉后贈王歷陽》:“謝尚自能鴝鵒舞,相如免脫鹔鹴裘。”詩中自比謝尚之放達,暗將王縣令比作嘆賞謝尚的王導;且指出正因王縣令的接濟,得免如相如般賣鹔鹴裘酤酒。對風神氣度的重視還體現在相如與衛玠、王獻之的并舉上。相如與衛玠的并舉重在“貌”。如宗楚客《安樂公主移入新宅》:“人疑衛叔美,客似長卿才。”相如與王獻之的并舉則重在“神”。如張南史《早春書事奉寄中書李舍人》:“神清王子敬,氣逐馬相如。”
其二,疾病書寫。從《史記》本傳中的“稱病”,到《西京雜記》所載因好色而得消渴疾,相如疾病書寫皆未及飲酒。相如、文君臨邛賣酒,以及《西京雜記》中相如賣鹔鹴裘為文君酤酒,才使相如與飲酒發生關聯。在唐代“事對”中,相如“病渴”逐漸衍化為“渴酒”這一帶有名士風度的癖好。杜甫《即事》將相如多病與阮籍好酒并舉是這種聯想的開始。白居易《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》:“慵于嵇叔夜,渴似馬相如。酒每蒙酤我,詩嘗許起予。”相如“渴”的內涵已由“消渴疾”轉換為“渴酒”。盧綸《酬崔侍御早秋臥病書情見寄時君亦抱疾在假中》:“元凱癖成官始貴,相如渴甚貌逾衰。”詩中征引相如渴病安慰崔侍御,顯然并非指好色,而是通過與杜預《左傳》癖并舉,強調崔侍御與自己皆為好酒成疾。這種轉換可歸因于“渴”字闡釋的多重性。羅隱《聽琴》:“不知一盞臨邛酒,救得相如渴疾無。”已將酒作為救渴良藥。
其三,文才展現。許渾《和賓客相國詠雪》:“道蘊詩傳麗,相如賦騁才。”謝道韞詠雪見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,相如賦雪出自謝惠連《雪賦》,許渾精準把握到兩個事典高雅趣味。盧照鄰《楊明府過訪詩序》:“豈使臨邛樽酒,歌賦無聲;彭澤琴書,田園寢詠。”將相如創作歌賦與陶淵明作田園詩并舉,顯示對名士風度與閑適生活的追求。
“事對”深入參與了漢賦紀事的經典化歷程。六朝“事對”確立了漢賦紀事接受的基本范式,唐代“事對”在繼承六朝獻賦、失志書寫的同時,促成漢代賦家的名士化轉向。而當唐人以時人與漢代賦家對舉時,“事對”的文學史意義又演進一層。鄭谷《蜀中三首(其二)》:“揚雄宅在唯喬木,杜甫臺荒絕舊鄰。”在詠嘆揚雄宅時,鄭氏并未以相如琴臺相對,而是選擇當朝典故“杜甫臺”。貫休在閱讀杜甫詩集時,也評價杜甫曰:“命薄相如命,名齊李白名。”當李、杜開始與馬、揚并舉,新一輪文學經典化歷程又在“事對”藝術中展開。(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)





 贛公網安備 36010802000294號
贛公網安備 36010802000294號 客戶端
客戶端 官方微博
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