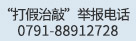
由江西省兒童劇院、太倉大劇院共同出品的兒童劇《鄭和·東方寶船》以明代航海家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為故事背景,將寶船上的重要物件如舵桿、鐵錨、火藥匣、牽星板、針灸包、銅燈、青花瓷等一一擬人化,賦予各類器物生命與個(gè)性,講述了小團(tuán)隊(duì)在啟航前夕發(fā)生的一系列故事,既有新老舵桿的交接、傳承過程,展示小舵桿的成長(zhǎng)線,也揭示了小團(tuán)隊(duì)內(nèi)部的矛盾,如牽星板在一次導(dǎo)航失敗被指責(zé)后心生愧疚與不滿,漸生心病,于是想方設(shè)法阻止此次出航,但最終在老舵桿的感化下重新融入團(tuán)隊(duì),講述了團(tuán)隊(duì)協(xié)作的重要性,間接描寫了當(dāng)年下西洋的種種困難與阻礙,也就更凸現(xiàn)出七下西洋的偉大不易。全劇有人物、有主題、有矛盾、有互動(dòng),演員表現(xiàn)力強(qiáng),且演員的服裝體型個(gè)性均與所扮物件貼近,如嬌小玲瓏活潑的青花瓷,扎實(shí)壯碩憨厚的大鐵錨等,是一部立意鮮明、制作精良、藝術(shù)精妙的兒童劇。
一、匠心獨(dú)具的劇本敘事結(jié)構(gòu)
全劇采用明暗雙線并行的敘事結(jié)構(gòu),明線講述鄭和船隊(duì)第七次下西洋前團(tuán)隊(duì)的準(zhǔn)備過程,暗線則聚焦小舵桿“小寶”從抗拒使命到接受責(zé)任的成長(zhǎng)歷程,巧妙地將歷史事件與童話故事融為一體,這種敘事設(shè)計(jì)既保持了歷史題材的宏大背景,又通過微觀視角和兒童心理闡述讓兒童觀眾產(chǎn)生情感共鳴。劇本還將歷史真實(shí)與藝術(shù)想象有機(jī)結(jié)合,在呈現(xiàn)鄭和下西洋基本史實(shí)的同時(shí),創(chuàng)作者大膽賦予船體主要部件以人格特征,比如驕傲聰明的小舵桿、睿智的老舵桿、暴躁的火藥匣、陰郁的牽星板等,這些擬人化角色的設(shè)置從角色個(gè)性和服裝配色上既保留了器物本身的特性,又具有各自鮮明的性格特征,使原本抽象的歷史事件和事物轉(zhuǎn)化為可觀、可感的童話故事和角色。
此外,劇本在時(shí)間處理上也匠心獨(dú)具,以古代計(jì)時(shí)的“夜游人”(打更人)報(bào)時(shí)作為分場(chǎng)標(biāo)志,從“子時(shí)”到“辰時(shí)”的五個(gè)時(shí)辰里,劇情經(jīng)歷了從眾人滿懷信心、新舵桿出現(xiàn),引發(fā)爭(zhēng)議、新舵桿不愿接手、新老舵桿談心轉(zhuǎn)變、眾人考核新舵桿、新舵桿再遇挫折迷茫、新舵桿躲藏不現(xiàn)身引發(fā)慌亂、老舵桿犧牲自己到全員齊心拉動(dòng)風(fēng)帆起航,層層推進(jìn)。包括序幕中觀眾參與的折紙船互動(dòng)也是劇本敘事的一部分——直入主題,讓現(xiàn)場(chǎng)小朋友們瞬間進(jìn)入寶船的戲劇情境。而隨著天光漸亮,編劇運(yùn)用一波三折之筆不斷升級(jí)戲劇沖突,最終在日出時(shí)分達(dá)到高潮——團(tuán)隊(duì)終于擯棄嫌隙,歸于齊心合力,這種時(shí)間與光線的象征性運(yùn)用,促成了該劇獨(dú)特的戲劇張力。
二、器物擬人化的角色塑造
本劇在角色塑造上實(shí)現(xiàn)了藝術(shù)突破,劇中的主要角色都取材于寶船的各個(gè)實(shí)際部件,各自被賦予豐富的人格特征和情感世界。小舵桿“小寶”是劇中的核心角色,擁有完整而真實(shí)的成長(zhǎng)弧線——從最初渴望成為天妃宮棟梁、拒絕成為舵桿,到經(jīng)歷迷茫、被槃伯的精神深深震撼,再到最終接受使命、帶領(lǐng)寶船起航,立誓成為“最棒的舵桿”。他的成長(zhǎng)轉(zhuǎn)變過程細(xì)膩又自然,直達(dá)人心。
老舵桿“槃伯”則是劇中領(lǐng)導(dǎo)者和指明燈的形象,作為曾六次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長(zhǎng)者,他兼具心理上成熟理智與物理上衰頹脆弱的雙重特性,既是傳統(tǒng)守護(hù)者,又不得不面對(duì)衰老、尋求繼任者的現(xiàn)實(shí)。第二場(chǎng)中他與小寶夜談的話語充滿人生哲理,如“全世界的海水都是相通的”等臺(tái)詞,既符合人物智者身份,又升華了劇作中和平外交的時(shí)代主題。篇末當(dāng)槃伯為了挽救斷裂的纜繩,最終與船帆融為一體時(shí),這種富有詩意的處理既悲壯又溫暖,既展示了他作為曾經(jīng)的領(lǐng)導(dǎo)者將矛盾的小團(tuán)隊(duì)重新彌合的重要作用,也展現(xiàn)了他作為一根舵桿在航海生涯中的生命輪回、天人合一的深刻寓意。
其他角色也都個(gè)性鮮明、各具特色,比如時(shí)時(shí)擔(dān)憂、總覺得自己和船員有病的針灸包“針姨”,嬌弱、害怕受傷的青花瓷“花花”,精瘦高挑、立場(chǎng)不堅(jiān)定的銅燈檠“亮亮”等,這些角色在保留器物基本功能特性的同時(shí),其存在的性格缺陷與成長(zhǎng)空間也為劇情發(fā)展提供了動(dòng)力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劇中牽星板“牽星”這一角色的設(shè)定,她因曾犯錯(cuò)導(dǎo)致寶船偏離航線而心懷愧疚、害怕與委屈,甚至憤而黑化,分化小團(tuán)隊(duì),但最終在團(tuán)隊(duì)包容下重回正軌、重獲信心,稱頌了團(tuán)結(jié)協(xié)作的重要意義。編劇客觀講述了牽星板黑化的原因,沒有片面去指責(zé)她的短暫叛變,而是從人性的角度去挖掘和理解,打破了兒童劇中角色非黑即白的簡(jiǎn)單化處理,展現(xiàn)了人性的多面性和復(fù)雜性。另外,劇本也不諱于展露團(tuán)隊(duì)的內(nèi)部矛盾以及人物個(gè)人的內(nèi)心糾葛,如船員對(duì)小寶的質(zhì)疑、牽星板對(duì)小寶的誘導(dǎo)以及小寶的自我迷茫等,無不增加了劇情發(fā)展的真實(shí)性和細(xì)膩度。
三、精巧創(chuàng)新的詩意舞臺(tái)表達(dá)
劇中借用快問快答、趣味問答形式巧妙普及了古代航海技術(shù)知識(shí),如牽星板導(dǎo)航、豆芽防治壞血病、水密隔艙設(shè)計(jì)等,這些內(nèi)容呈現(xiàn)既具科普價(jià)值又不失戲劇性。而現(xiàn)場(chǎng)觀眾參與折紙船、學(xué)習(xí)航海技能、協(xié)助升起風(fēng)帆等多次互動(dòng)環(huán)節(jié)設(shè)計(jì),主動(dòng)跳出第四堵墻,打破了舞臺(tái)與觀眾席的界限,實(shí)現(xiàn)了真正意義上的參與式劇場(chǎng)。
除了話劇式的舞臺(tái)表達(dá)模式,劇中還融入了歌曲的表達(dá)。主創(chuàng)設(shè)計(jì)了數(shù)首風(fēng)格各異的原創(chuàng)歌曲,如《等天放亮就將起航》的朝氣昂揚(yáng),《自以為是真可笑》的戲謔調(diào)笑,《方向》的迷茫憂傷,《東方寶船》的恢弘壯麗等,這些音樂緊密貼合劇情事件,有效推動(dòng)劇情發(fā)展,同時(shí)強(qiáng)化了角色們的情感表達(dá),豐富了舞臺(tái)藝術(shù)表演和表現(xiàn)空間。而劇中反復(fù)出現(xiàn)的“嘿呦”的勞動(dòng)號(hào)子,既是對(duì)傳統(tǒng)船工文化的還原,也創(chuàng)造出觀眾參與的互動(dòng)契機(jī),瞬間便將單一的劇場(chǎng)空間轉(zhuǎn)化為共享的儀式場(chǎng)域。
此外,該劇的舞臺(tái)美術(shù)設(shè)計(jì)也極具創(chuàng)意,如以船帆、桅桿、階梯、底艙等道具將寶船部件解構(gòu)重組成高低錯(cuò)落的藝術(shù)裝置,既保留了船的意象,又突破了寫實(shí)限制。而在第六場(chǎng)纜繩斷裂危機(jī)中,槃伯將自己系在繩索間的場(chǎng)景,通過身體表演與舞美裝置的互動(dòng),創(chuàng)造出令人震撼的視覺隱喻。又如第四場(chǎng)中眾人在指責(zé)牽星板出錯(cuò)時(shí),主創(chuàng)巧妙將指責(zé)的話語以音效的形式具象化成一聲聲響亮的耳光,將牽星板的愧疚和怨恨表現(xiàn)得具體而微。
多媒體技術(shù)的運(yùn)用更是直接拓展和升級(jí)了本劇的地域和文化表達(dá)空間。紗幕上投射的“太倉”“占城”“蘇門答臘”等古地名,東方寶船的構(gòu)造結(jié)構(gòu)、鄭和身影與天妃宮廊柱的虛實(shí)相應(yīng),以及尾聲展示的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路線圖,共同構(gòu)建起一種跨越時(shí)空的詩意對(duì)話。這種舞臺(tái)處理方式不僅滿足了兒童對(duì)視覺奇觀的期待,還潛移默化地傳遞了歷史文化信息。
四、兒童教育方式與價(jià)值的深層建構(gòu)
與傳統(tǒng)兒童劇不同,《鄭和·東方寶船》的教育價(jià)值體現(xiàn)在深層次的心理建構(gòu)而非表面化的道德說教。劇本通過小寶的成長(zhǎng)歷程,探討了責(zé)任與夢(mèng)想的關(guān)系這一永恒命題。小寶從“我是鐵力木,我可是鐵力木!”到“我要成為最棒的舵桿”的宣言,展現(xiàn)的是他從自我中心到團(tuán)隊(duì)意識(shí)的轉(zhuǎn)變,這一過程對(duì)正處于社會(huì)化關(guān)鍵期的兒童觀眾具有重要啟示意義。
劇中設(shè)計(jì)的“登船考試”“模擬航行”等情節(jié)具有一定的教育智慧。快問快答環(huán)節(jié)傳遞航海知識(shí),絕對(duì)指令環(huán)節(jié)培養(yǎng)學(xué)習(xí)、服從和領(lǐng)導(dǎo)能力,模擬航行環(huán)節(jié)考驗(yàn)危機(jī)處理,這種游戲化設(shè)計(jì)符合兒童認(rèn)知特點(diǎn)。特別是在小寶指揮失誤時(shí),劇本并未簡(jiǎn)單否定他的錯(cuò)誤,而是通過對(duì)比槃伯的應(yīng)對(duì)策略,展現(xiàn)一名合格領(lǐng)導(dǎo)者所需的沉著、包容與智慧,引導(dǎo)兒童觀眾正確思考,這種呈現(xiàn)方式遠(yuǎn)比直接說教更為深刻、有效。
劇本中對(duì)于失敗與錯(cuò)誤的寬容態(tài)度尤為可貴,具有一定的現(xiàn)實(shí)觀照和反思意味。牽星板因曾經(jīng)犯錯(cuò)而自我懷疑,最終在團(tuán)隊(duì)接納中重獲信心;小寶經(jīng)歷指揮失誤后,團(tuán)隊(duì)給予改進(jìn)機(jī)會(huì)而非一味指責(zé)。這種“容錯(cuò)教育”對(duì)培養(yǎng)兒童抗挫折能力具有重要意義。而劇中“就算犯過錯(cuò),只要迷途知返,就永遠(yuǎn)都是東方寶船上最棒的一部分”的臺(tái)詞,更是直擊現(xiàn)代兒童成長(zhǎng)教育的核心。
劇中對(duì)于“和平友好”這一鄭和精神內(nèi)核的詮釋最為精妙,通過槃伯之口講述“鄭和大人奉皇帝旨意下西洋,就是為了宣揚(yáng)德化,結(jié)交朋友”“寰宇之內(nèi),我們都應(yīng)該做朋友”,包括僅通過投影而呈現(xiàn)的鄭和所說的“寶船啊……你承載著中華的榮耀,肩負(fù)著傳播文明之重任”“航海之人,本就該歸于滄海”等,這些表達(dá)將“人類命運(yùn)共同體”和“21世紀(jì)海上絲綢之路的和平合作理念”等當(dāng)代價(jià)值理念與古代航海家的實(shí)踐智慧相連接。
《鄭和·東方寶船》通過器物擬人化的創(chuàng)新敘事,將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題材轉(zhuǎn)化為兒童喜聞樂見的戲劇形式,在保持歷史真實(shí)性的同時(shí)展現(xiàn)了豐富的藝術(shù)想象力,兼具藝術(shù)性與思想性、娛樂性與教育性。它沒有將兒童視為被動(dòng)受教育者,而是通過平等的藝術(shù)對(duì)話,通過互動(dòng)等方式激發(fā)兒童對(duì)歷史文化的內(nèi)在興趣。當(dāng)孩子們手持紙船與舞臺(tái)上的“東方寶船”一同起航時(shí),種下的不僅是對(duì)歷史的認(rèn)知種子,更是對(duì)和平、勇氣、責(zé)任、團(tuán)結(jié)等精神價(jià)值的深刻認(rèn)同。這種“潤(rùn)物細(xì)無聲”的美育方式,無疑正是《鄭和·東方寶船》留給江西當(dāng)代兒童劇創(chuàng)作的珍貴啟示。
(作者單位: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)





 贛公網(wǎng)安備 36010802000294號(hào)
贛公網(wǎng)安備 36010802000294號(hào) 客戶端
客戶端 官方微博
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